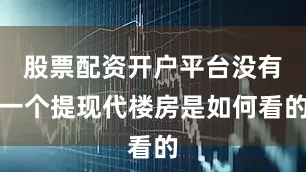我住的这地方,叫城市。楼高得抬头看,脖子发酸。路上车一辆撵着一辆,喇叭声就没断过。树是有的,草坪也绿,可就是少见鸟。偶尔飞过一只麻雀,也是慌慌张张,落一下就走,不像老家的燕子,认准了你家屋檐,就年年回来住。
老家不一样。每年春天,屋檐底下那对老燕子准到。它们不敲门,也不打招呼,可你一抬头,就看见泥窝边上探出两个小脑袋,黑亮的眼睛盯着你,像是在说:“我们又回来了。”我站在那儿,仰着头,没说话。它们在叫,我在听。
前年秋天,老屋塌得厉害,墙裂得能伸进手指头,檩子也朽了,只好拆了重盖。我心里头一直放不下:燕子的窝,就在东屋檐下,那可是它们住了好几年的家。它们飞走的时候,哪知道这房子要拆?我总想,等明年开春它们从南方回来,扑棱着翅膀绕一圈,窝没了,家也没了,该往哪儿落脚?
可第二年刚立夏,我拎着包走进院子,抬头一看——心“咚”地跳了一下。新屋檐下,那个泥窝又回来了,湿漉漉的,边缘还沾着草屑,一看就是刚修的。两只燕子停在电线上,见我进来,忽地腾空而起,在我头顶盘了两圈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像在打招呼:“你迟了,我们可没迟到!”
我站在那儿,没动,也没笑,只觉得鼻子一酸。它们竟真找回来了。砖是新的,墙是新的,可它们还是把家安在了原来的位置,分毫不差。我仰着头,看它们像剪子一样利落地划过蓝天,忽然明白:有些东西,人记不住,鸟记得。
展开剩余62%小时候,夏天的晚饭总摆在院子里。一家人围坐着,蒲扇摇着,锅里还温着绿豆汤。天一擦黑,蚊子就出来了,可还没等叮人,早被头顶飞着的燕子一口叼走了。奶奶说:“燕子不吃咱的粮,专吃害虫,是自个儿请来的护院。”她还说,燕子认家,谁家心善,它就往谁家飞。
有一年秋收,谷子晒在东房顶上,一群麻雀呼啦啦飞来偷食。正啄得起劲,突然几只燕子从屋檐下冲出来,翅膀拍得呼呼响,像小鹰扑兔,吓得麻雀四散逃命。打那以后,再没人敢说燕子碍事。我蹲在墙根下看它们飞,心里头悄悄敬着:这么小的身子,也有脾气,也有担当。
燕子长得也好看。通身乌黑,油亮亮的,像谁拿黑漆细细刷过;尾巴分叉,像一把小剪子,裁风裁云,裁出一道道弧线。飞起来时,身子轻得像没重量,时而滑翔,时而俯冲,一个转身,就钻进屋檐的阴影里,快得只留下一道影子。我常想,要是人也能这样飞,不为赶路,就为看看脚下的田、院里的树、屋上的烟,该多好。
它们搭窝更是讲究。一口泥,一口唾沫,从水坑边衔来,一点点往上糊。夫妻俩轮流出门,早出晚归,刮风下雨也不停。那窝半嵌在墙角,像半个碗,外头结实,里头铺着软草,暖和又安全。我蹲在底下看过,那泥一层压一层,密密实实,比人砌的砖缝还严。后来我在城里看见工人砌墙,一砖一瓦垒高楼,忽然觉得,他们和燕子,干的是一样的活——都是用双手,一点一点把“家”立起来。
最让我服气的,是它们认路。每年秋风一起,它们就带着小燕子飞往南方。千里万里,山高水长,可只要春风吹过麦田,第一声鸟叫响起,它们准到。不早,不晚,就像掐着日子回来报信。奶奶说,燕子南飞不是怕冷,是北方冬天没虫吃。它们飞那么远,为的是活命,可再苦再累,也不忘回头看看来时的路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:“燕子不落无主之家。”它们不挑富贵,不嫌贫寒,只要屋檐下有烟火气,有善心人,它们就愿意住下来。它们飞的不只是季节,是记忆,是念想。
如今我在城里走,偶尔抬头,看见电线上的黑点,总要愣一下——是不是它们?可再仔细看,不是,是麻雀,或是鸽子。它们飞得低,飞得慢,不像燕子,一划就是一道线,干脆利落。
但我还是抬头看。
因为我知道,只要老家的屋檐还在,燕子,就一定会回来。
□任学明
(责编:马云梅)
发布于:山西省七星配资平台-配资操盘开户-在线配资网站-配资平台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